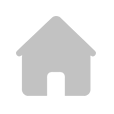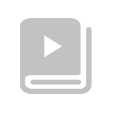提单物权凭证说,可以说是国内学说早期照搬英国法看法的结果,一旦引入,就如缠绕不休的幽灵扎根于大家的思想之中,成为大家的固有观念。尽管发现存在问题,大家亦宁可以不一样的讲解予以维护。笔者并不奢盼可以彻底改变这一业已根深蒂固的观念,但亦期望可以在本文中依据民法的基本理论为澄清问题提供一点线索。
非常早以前,已经对国内学界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提单性质的主流看法——提单为物权凭证,有不一样的怎么看。无意中在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的中国审判平台的留言版上看到以下帖子(http://www.ccmt.org.cn/bbs/bbsShow2.php?postBoardID=1&articleID=757),顿觉有必要就提单为物权凭证的看法作点澄清。该帖子的内容如下:
作者seagull留言:我感觉理论上将提单性质和功能分开理解是正确的,但假如说“提单只可能是债权证券”,在论证依据上好像并不充分。另外学生有以下疑问期望专家、老师们指教:1、假如说提单是债权证券,则其与票据性质上就相同,那样提单就应该具备完全的流通性,提单出售就是提单流通,提单象票据一样也应可以适用善意获得规范,但现在理论界好像并否认此点。2、提单的可出售性是基于提单可以代表货物。假如说提单在性质上是债权证券,怎么样理解提单可出售性的内涵呢?提单的这种“债权”性质与“物权”功能怎么样协调?对于商业实践和司法实践有什么意义?3、假如说提单是债权证券,怎么样讲解多份正本提单并存的状况呢?承运人的交货义务是否也就成了“绝对”的凭单交货了?
回复seagull的greentea则留言:看来你真的是认真考虑了。建议你看一下郭瑜的《提单法律规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非常不错的一本书。
第一对于greentea的留言有一点笔者深表同意,郭瑜老师著的《提单法律规范研究》确是非常不错的一本书。在该书中,郭瑜老师以国内现行法律为依据,否定了提单为所有权凭证的看法;在否定提单所有权凭证说后,郭瑜老师进一步提出了提单所代表的权利为“推定直接占有权”的倡导。
在提单性质的问题上,笔者觉得,提单物权凭证(或物权证券)说中的所有权凭证说无视现行法律定义及体系,予以否定乃属当然,郭瑜老师否定提单为所有权凭证,值得同意,这一论述应当说已走出了关于提单性质认识误区的要紧一步,在此不予详论(详细论述见郭瑜老师在《提单法律规范研究》中的论述);但笔者对郭瑜老师有关提单所代表的权利为推定直接占有权的看法另有不同怎么看。为此,本文将第一着重对郭瑜老师有关推定直接占有权的倡导进行评析,继而再提出笔者的个人见解。
1、讨论提单性质的目的
在民法学上,常常讨论各种法律现象的性质,譬如悬赏广告的性质(要约还是单办法律行为)、无因管理的性质(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合同解除恢复原状义务的性质(不当得利返还义务还是二次给付义务)、优先购买权的性质(请求权还是形成权)等,当然提单性质亦是讨论最多的性质问题之一。
为何要讨论法律现象的性质?确定某法律现象的性质,其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据以确定所讨论法律现象的法律适用。譬如,讨论悬赏广告的性质,在于确定悬赏广告是不是适用合同法上要约、承诺的规定,从而确定法律行为规定是不是适用于行为人的行为,其中非常重要的是要确定行为人是不是须拥有行为能力,或了解悬赏广告内容,方能获得对广告人的权利;讨论合同解除恢复原状义务的性质,目的在于确定恢复原状义务与合同解除前的义务是不是为同一义务,合同解除前义务上的担保,是不是及于恢复原状义务,同时亦可确定诉讼时效的计算办法[2]。另外,也可通过依据法律现象在法律适用上的有关特征,对其进行概括并确定其性质,以便于大家可以概括的方法通过学会其性质而知道该法律现象在法律适用上的各方面特征。譬如,学会票据在性质上是资金债权有价证券,只须是知道有价证券及资金债权理论的,即是否了解:(1)持有人持有票据即享有其代表的资金债权,(2)丧失票据即没办法行使其代表的资金债权,(3)票据所代表的债权原则上不可以以出售票据以外的方法获得,及(4)票据所代表的债权原则上不发生履行不可以的问题[3]等。其中第(1)至(3)项为有价证券的体现,第(4)项则为资金债权的体现。又譬如,只须学会公司与其董事之间关系在性质上是委托合同关系,即可知董事处置公司事务时具备过错的,公司可需要董事承担赔偿责任(《合同法》406条);董事为公司垫付处置公司事务的成本时,可需要公司偿还(《合同法》398条);董事在处置公司事务时,应根据公司指示(《合同法》399条)等。
据上所述,讨论提单性质的目的即在于:一方面,确定提单适用何种法律规范,如将提单确定为物权凭证(亦即物权证券或物权有价证券),则提单即应适用物权及有价证券的法律规定。从而,基于提单有价证券的属性,提单物权因持有提单而获得,因丧失提单而丧失;基于提单权利的性质为物权,则提单权利的得丧变更应适用物权得丧变更的规定,权利受侵害时适用物权被侵害的规定。其次,则在于便利大家以概括的方法,通过学会提单的性质以学会提单在法律适用上的各方面特征。
2、本文对提单代表“推定直接占有权”的理解
郭瑜老师觉得,可以将提单表彰的物权明确规定为一种推定直接占有权,而这种推定直接占有权和提单本身结合在一块,持有提单即享有这种占有权,丧失提单也就丧失这种占有权,提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称为“物权证券”。对郭瑜老师的上述看法,可分以下数项予以剖析:
(1)提单是一种有价证券,其所代表的利益与提单本身结合在一块,提单利益因持有提单而享有,因丧失提单而丧失。
(2)提单所代表的利益为对货物的直接占有权,持有提单即享有对货物的直接占有权,丧失提单即丧失对货物的直接占有权。
(3)持有人因持有提单而享有对货物的直接占有权,是一种法律上推定的权利。但本文觉得,更准确的应该是法律上拟制的权利。笔者推断,郭瑜老师所说的推定,并不是证据规则上的推定,而是指提单持有人本未直接占有货物,但法律上拟制提单持有人直接占有货物,并在法律上处于货物直接占有人的地位。
(4)提单所代表的推定直接占有权在性质上是物权,提单因此是物权证券。
对于上述有关提单所表彰的利益为推定直接占有权,从而觉得提单为物权证券的看法,可称之为“提单直接占有权物权凭证说”,与提单所有权凭证说、提单债权凭证说相不同。
3、提单代表直接占有?
笔者在本部分第一依据占有及有关规范的基本理论,对提单所代表的利益是不是确为占有,甚至应否为占有些问题进行讨论。
在倡导提单代表直接占有些看法中,一般均从提单持有人的角度说明其基于持有提单而获得的权利,却总是忽视了在这一学说下对货物的实质直接占有人的影响。在提单直接占有权物权凭证说下,对货物的直接占有被证券化而与提单相结合,基于法律的拟制,持有人因持有提单而享有对货物的直接占有,持有人因丧失提单而丧失对货物的直接占有。至于对货物的实质直接占有人而言,譬如承运人或基于承运人意思而直接占有货物的人(如实质承运人、码头运输人等)以至货物的非法占有人(如从承运人处侵夺货物的人、基于无单放货获得货物的人等),在立法政策上则存在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以实质直接占有人的直接占有与提单持有人的直接占有并存,即在同一货物上同时存在两项直接占有;二是不是定实质直接占有人的直接占有,即实质直接占有人在法律上并不享有直接占有人的地位,仅提单持有人享有该地位。
就实质直接占有人的直接占有与提单持有人的直接占有并存而言,该看法承认在一物上可以同时存在两项或以上的直接占有,从而实质直接占有人与提单持有人各自的直接占有得分别依据法律规定发生效力(以直接占有为要件的事情的效力)。譬如,在提单持有人为货物所有权人并通过提单而直接占有货物的同时,或于提单持有人将货物出卖于买受人并通过出售提单而出售其所有权的同时,货物实质占有人的实质直接占有可作为获得时效起算要件而引起获得时效的起算(如承认获得时效规范),实质占有人向第三人出卖货物并移转其实质直接占有(即出货)得作为善意获得的构成要件(如承认善意获得规范)等。最后将可能出现提单持有人或从提单持有人获得提单的人,与实质直接占有人(包含从原实质占有人受让实质直接占有些人)同时获得并享有货物所有权的状况,发生两者之间的冲突,显然违反一物一权的物权法基本原则[4]。除非觉得一物一权原则并无适用空间,不然提单持有人的直接占有与实质直接占有人的直接占有得以相并存的看法,并无立足的空间。
就否定实质直接占有人的直接占有而言,此看法将致使事实上的直接占有不具备直接占有或占有些效力,从而实质直接占有人的直接占有亦丧失其公示效力。譬如,善意获得人即使直接占有货物亦因其占有不构成占有而没办法基于善意获得规范获得货物所有权(如承认善意获得规范),实质直接占有人亦没办法依其占有而依据时效获得规范获得货物所有权(如承认时效获得规范)。这将破坏实质直接占有些公示功能,亦破坏以占有为动产的基本公示方法的物权有关规范的体系。
这样来看,无论是直接占有人的直接占有与提单持有人的直接占有同时并存,还是因提单持有人的拟制直接占有而否定实质占有人的直接占有,均没办法与固有些物权有关规范协调。归根结底,问题在于直接占有作为占有人对其物推行实质管领的事实,在性质上根本不适于被拟制。直接占有在事实上具备排他的属性,在物权有关规范上具备举足轻重的功能,一旦就同一物在事实上的直接占有外拟制另一项直接占有,将对固有些物权有关规范导致很大的破坏。
假若觉得在立法政策上可通过拟制确认提单持有人的直接占有,因为此拟制将涉及固有物权规范的公示原则,以至一物一权的物权法基本原则,故起码亦应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仅于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的债权合同关系,固然可依据意思表示讲解规则,将国际惯例作为当事人的意思而予以适用以确定其内容,但对于提单持有人直接占有些拟制,即使国际上存在以提单所代表的利益为直接占有些惯例,亦不应通过此国际惯例予以确立。更何况在比较法上好像根本没有一般性地拟制提单持有人直接占有些立法例。常常被引用并被学者视为承认提单物权效力规定的台湾民法629条,其规定为“出货提单于有受领物品权利之人时,其出货就物品所有权移转之关系,与物品之出货,有同一之效力”,只不过规定了在物品所有权关系中,提单的出货才具备与物品之出货的同一效力。也即只有在移转物品所有权时,出货提单才等同于物品本身的出货,而得发生所有权变动的效力,远非一般性地拟制持有提单即享有货物的直接占有,更不可以据此而认提单为代表对货物直接占有些有价证券[5]。
4、提单代表间接占有?
提单所代表的不是也不应是对货物的直接占有或直接占有权,已如上述。或有觉得,提单所代表的利益仍为占有,只不过并不是直接占有而是间接占有,此见解可称为“提单间接占有凭证说”。提单是不是为间接占有凭证,应视乎提单持有人合法持有提单,是不是即享有提单下货物的间接占有。对此问题,应依据间接占有些成立要件作出判断。
间接占有些成立,一须直接占有人基于肯定占有媒介关系(如出租、质押等法律关系)而为占有,二须直接占有人有为间接占有人占有些意思(即他主占有些意思),三须间接占有人于占有媒介关系消灭后对直接占有人有返还占有物请求权。其中需小心的是第二项要件,即间接占有些成立须直接占有人有他主占有些意思,如直接占有人改变他主占有些意思,而变为自主占有(侵夺占有物),间接占有即归消灭[6]。除此之外,在多阶层的间接占有中,上阶层间接占有尚须各下阶层与其下阶层或直接占有人之间亦均拥有所有间接占有些要件[7]。如在承租人转租出租物的情形,出租人间接占有些成立不只须其与承租人之间拥有间接占有些成立要件,还需要承租人与转租承租人之间拥有间接占有些成立要件,如转租承租人侵夺出租物而变为自主占有,不只承租人的间接占有消灭,出租人的间接占有亦告消灭。而在承租人无权处分出租物而将占有移转时,受叫人亦非以他主占有些意思而占有,承租人对出租物不构成间接占有,出租人亦丧失其间接占有。
提单是不是为表彰间接占有些有价证券,取决于提单合法持有人是不是因持有提单而即拥有上述三项要件并成为间接占有人。从上述间接占有些成立要件看,只有第一项和第三项要件在性质上可由有价证券予以表彰。持有提单即表明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存在占有媒介关系,并表明持有人对承运人享有货物返还请求权。但,对于承运人的他主占有意思,则根本不可以通过提单予以表彰。只须承运人否定其他主占有意思,或无权处分货物,即使持有提单也不可以代表持有人享有对货物的间接占有。同时,在多阶层占有些状况,提单本身亦没办法表彰承运人与其下阶层占有人或直接占有人之间成立间接占有,只须下阶层任何一个环节不成立间接占有,提单持有人即丧失间接占有。这样来看,间接占有这一法律现象,在性质上本非得以由有价证券予以表彰。这样来看,持有提单并不是享有对货物的间接占有,提单并不是间接占有凭证。
另须说明的,是提单间接占有凭证说的成立,尚须取决于法律是不是承认间接占有些地位,即承认间接占有得遭到与直接占有相同的保护。间接占有与直接占有毕竟不同,直接占有为事实上的占有,占有人对其物有事实上的管领力,间接占有则为一种观念上的,亦即拟制的占有,间接占有人事实上的管领力相当薄弱。间接占有是不是应与直接占有遭到相同的保护,为立法政策问题,在国内物权法草案的学者建议稿中,即未承认间接占有。若立法上否认间接占有,提单间接占有凭证说也无成立的空间。
4、占有为物权?
除此之外,即使有关提单代表推定的直接占有权或间接占有些看法成立,尚需要占有或占有权确实为物权,关于提单为物权凭证的倡导方可成立。但,占有真的为物权吗?
从比较法角度看,彼帮或彼岸在学说上就占有是不是为权利有激烈争论的,如德国、台湾;亦有因法律有明确规定,占有为权利已为定论的,如日本。不过,应该注意的,是无论在德国、日本还是台湾,学说主要讨论的,是占有是不是为“权利”,而不是占有是不是为“物权”,或法律规定的,是占有为“权利”,而不是占有为“物权”。
先就占有是不是为权利而言,日本民法因为继受法国立法例而采“占有权”的定义,学说以占有为权利,并无争论。至于德国民法未将占有规定为“占有权”,占有到底为权利抑为事实,学说争论甚大,但以事实说为通说。台湾学界从德国学说,亦以事实说通说。占有为权利还是事实,其不同的意义体目前若干方面。如占有仅为事实而非权利,则占有不能为确认之诉的标的,不能为对抗强制实行的依据[8],最主要的,在于占有在遭到侵害时倡导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依据。日本民法明确规定占有为权利,其在侵权行为法上的后果为占有人于占有被侵害时,可依据日本民法709条需要加害人承担侵权责任。至于德国、台湾民法,是不是将占有定性为权利,决定着占有人的占有被别人侵害时,到底得依据权利侵权(德国民法823条1项、台湾民法184条1项前段)还是利益侵权(德国民法826条、台湾民法184条1项后段)认定加害人的责任,对占有人利益影响重大。如占有为权利,则占有加害人侵权责任的构成以其具备故意或过失为要件;如占有不是权利,则加害人责任不适用权利侵权规定,而适用以故意违反善良风俗办法加害于别人的规定[9]。在德国、台湾民法,有关占有性质的讨论,主要目的在于解决侵权责任规定的适用问题。而在国内现行法下,因为并未使用像德国、台湾民法的侵权责任体系,占有是不是权利对于侵害占有侵权责任的认定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即使在结论上觉得占有得成为侵权客体,在国内侵权行为法下亦无须将它先界定为权利,其所被界定为的,应为财产(《民法通则》106条2款)。而即使要在财产这一概括定义下对侵权客体进行种类化,完全可以将占有作为一种独立的财产种类,无探讨其到底应界定为事实抑或界定为权利的必要。
退一步说,即使觉得应付国内侵权行为责任体系作好似德国、台湾民法的区别,将侵权区别为权利侵权及利益侵权,前者以故意或过失为要件,后者则须以使用故意违反善良风俗办法为要件,从而使对占有界定为事实或权利具备必要,也不可以得出占有即当然为权利的结论。依据德国、台湾主要学说,占有作为事实而非权利,本不适用权利侵权的规定,仅在特定条件下方被认定为权利而适用权利侵权规定。而该特定条件,主如果指在有权占有些情形,占有人依其权原,得对占有物为特定范围之用收益时,因为此种就特定权原所生用收益之权能,与占有结合之时,强化了占有之地位,使占有人处于类似物权人之地位,如承租人、典权人、地上权人的占有。在此情形下,因为占有人的占有与其基于权原的权能相结合,使占有人的占有,不同于一般无基于权原就标的物享有用收益权的占有,方基于价值判断将它认定为权利,适用权利侵权的规定。至于无权占有、占有人无用收益权能的有权占有,均不作为权利而适用权利侵权的规定[10]。参考德国、台湾学说,法律既未将占有界定为权利,假如需要对占有进行界定以认定侵权行为的种类,占有在价值判断上亦非在任何状况下均适于被界定为权利,也就是说,将占有界定为权利是有条件的,不然,占有在不少场所仍仅被认定为事实而非权利。
[1][2]下一页